本篇对话自始至终都充盈着一股精神的内力。正如责任编辑所说,《云中记》对她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牵引和震撼。
对于一部完成度较高、非常成熟的名家作品,编辑还能做些什么?本篇对话提供了一个示例,从中希望体现的是编辑存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内涵和外延。或许,编辑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文字的专业加工,以及装帧设计之类技术性、流程性的工作上,更主要体现在与作者的心灵契合上。作为第一读者,与作者共同经历了一次心与心的相通,由此再造文化、意境、思想、精神体验(产品)的过程,就是编辑的重要价值。
编辑力的养成,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在编辑过程中进入并享受作品的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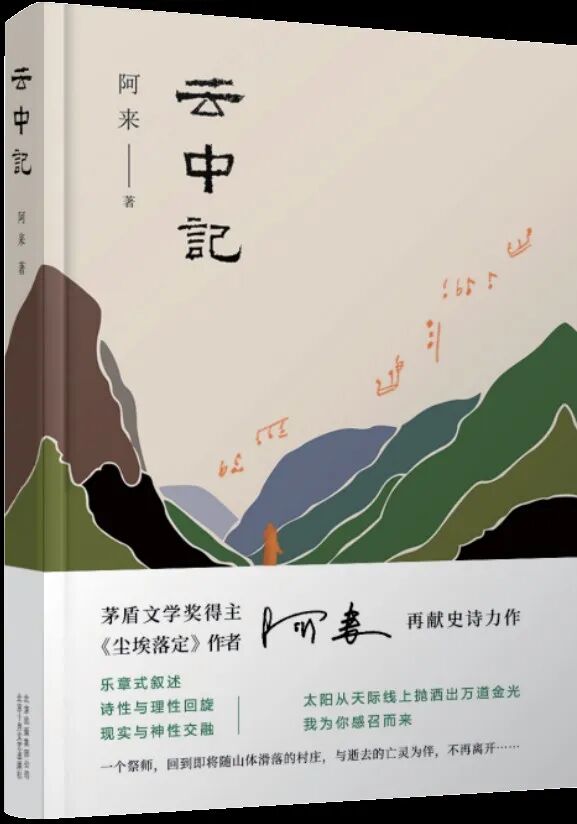
《云中记》
阿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
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图书奖
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入选2019 年度“中国好书”

王淑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云中记》责任编辑
策划编辑有《穆斯林的葬礼》《平凡的世界》《云中记》《平安批》《宝水》等
寻找选题的“鲁冰花”
伍旭升:名家、重大灾难事件、可以预期又令人满怀期待的玄妙文本……总之,是否一眼就相中了这本书稿?
王淑红:名家确实很重要。我刚来社里的时候,总编辑韩敬群老师就给我讲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主要产品线,名家力作是很重要的一条。而且,阿来老师不是一般的名家,他对于我来说,还有特殊的意义,他为我开启了文学之门。2000年的时候,我在读大学,就有人给我强烈推荐《尘埃落定》,说这是茅盾文学奖中极好的作品。我是一个中文系学生,在这之前也读过一些小说,但好像一直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直到读《尘埃落定》,仿佛突然被一种美与精神之光照亮。从此,文学在我心中有了一种神圣之感。阿来这个作家,在我心中也成为一个文学高地的象征。
但《云中记》之所以打动我,并不是因为重大灾难题材,而是它的精神感召力。我还记得阿来老师第一次给我讲述《云中记》,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时候,他刚刚有了《云中记》的构思。看得出来,他很激动。他说,藏族的村子里都有一个巫师,负责祭祀山神,安抚亡灵。汶川地震时,有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子,伤亡两百余人。地质勘探发现,这个村子处在一条滑坡带上,最终会和滑坡体一起坠入岷江。政府组织了整体搬迁,把村子搬到平原。可是随着时间过去,村里的巫师感到内心越来越不安。他想,活着的人都有政府照顾,那么那些死去的人呢?没有人安抚他们,不是太可怜了吗?于是他决定回到那个即将滑坡的村子,祭祀山神,安抚亡灵。阿来老师给我翻开一本摄影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位巫师一个人在做法事。这个人就是《云中记》主人公阿巴的原型。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他在汶川地震后,每年都会回到山上的村子,去安抚亡灵。总有一些人跟随内心的声音,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人好像在替我们走想走而没有走的路,替我们过想过而没有过的人生。照片里的巫师是这样,《云中记》里的阿巴是这样。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深深打动了我,超越题材,超越情节,直达内心深处。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绘本编辑的时候,我编过一个绘本,叫《花婆婆》。花婆婆小时候,对外公说长大后想要做什么,外公说好,但是别忘了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后来花婆婆长大了,她做了很多想做的事。后来她老了,在海边的房子里住下来,想起了外公说的,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于是她买了很多鲁冰花的种子,每天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撒在草地上,撒在角落里。大家不知道她在干什么,都叫她“疯婆婆”。后来到处都开出了紫色的鲁冰花,美极了,大家就叫她“花婆婆”。
我希望我编辑出版的图书,也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书,《云中记》就是这样的书。
阿来老师不但写出了《尘埃落定》,还写出了《空山》《格萨尔王》《蘑菇圈》等,文学品质都非常高。我从来不担心他的作品的文学性。所以,我一听他讲《云中记》的构思,就知道这会是一本奇妙之作,是天才作家也难得一遇的神来之笔。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内心充满了感恩。
伍旭升:你的讲述让我也深受感染。的确,我读后也非常认同你的判断和感受。那么,对选题价值的判断,一般依据什么指标?有没有符合这些指标,期待值挺高,市场却不认可的情况?
王淑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以出版原创文学作品为主的文艺出版社。我们对于选题价值的判断,首先是基于文学价值的判断,其次要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效益,一方面是经济效益,当然最好是两个效益都好。但实际情况是,市场是难以预期的,而纯文学作品的市场又格外冷淡些,获奖作品也永远是少数。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幸运,做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刚才说到十月文艺的产品线,名家力作是一条,青年作家的精心之作也是一条,对编辑也没有单一考核利润,编辑们可以相对从容地挑选符合自己审美追求的作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向提倡温暖而开阔的现实主义,我个人的追求也与此契合。某种程度上,我的编辑工作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因为本质上,我种的不是活命的粮食,而是赏心悦目的花朵,我只管松土、浇水、除虫,静静等待它成长。这个过程已充满了满足感,所有花朵都是额外的奖励。
伍旭升:说说这本书稿是怎么组到手的吧。
王淑红:《云中记》是我跟踪阿来老师多年的幸运相遇。从第一次约稿,到签下《云中记》,跨越了六年的时间。还记得第一次约稿是一个春天,我到南充出差,就想都到四川了,试试看能不能拜访阿来老师吧,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自报家门。正好他在,说有两个家乡的朋友也过来找他,那就一起见吧。他带我们到一个好像是叫梅园的地方吃午饭,窗外院子里春绿已浓。席间来了一个弹唱的藏族小伙子,唱着可能是藏族的民歌,低回悠扬。阿来老师和他家乡的两个小伙子跟着唱起来。那次我跟他讲了《尘埃落定》对我的影响,并表示了出版他作品的意愿。他跟我说,这本书当年被很多家出版社退过稿,也包括你们社,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并且当重点书报了茅盾文学奖。所以,只要当年那个编辑还想出,就会让她在的那个出版社来出版。
我一点都没有失望,反而非常感动,对阿来老师充满了更深的敬意。别人的美好总会让我们对世界充满信任,对人生充满希望。实际上,《尘埃落定》的版权在那位编辑退休前,就一直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所以,这样的作者才会看重阿巴这样的人吧,才会写出《云中记》这样的作品吧。
后面的几年时间里,我就主要跟踪阿来老师的新作了。那时知道他在写一部关于洛克的长篇小说,他也同意给我们出版,但就是迟迟没能签约。直到2018 年5月,他准备放下那个长篇,写《云中记》了。在还仅仅有构思的时候,我们就签订了出版合同。阿来老师为什么会把这部书稿交给我们出版社出版?我想大的原因肯定是相信我们的品牌,相信我们的发行能力。此外,阿来老师还说过,是因为我们跟得最紧。
一曲庄重的安魂曲
伍旭升:与阿来老师之前熟悉吗?拿到书稿时你是什么心情?之后与阿来的第一次交流,你又是什么心态?都交流了什么?
王淑红:在第一次约稿之前,我与阿来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云中记》签约后,我就一直满怀期待地等待。几个月后,阿来老师告诉我,写完了初稿,但是还要改。我说我先看看,保证不提意见,不干扰他的修改,他不同意。我就只好继续等着。后来有一天,他说改完了,正好要来北京,拿来给我看。所以第一次看《云中记》的稿子,是在阿来老师的酒店房间里,在他的电脑上,他就坐在后面抽烟。
《云中记》是向地震中的死难者和消失的城镇与村庄的献祭,是一曲庄重的安魂曲。
后面开篇是:“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山壁粗粝,植被稀疏,石骨裸露。”小说展开叙述,准确,清晰,简明,沉静。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读了一部分,没有评价。我跟阿来老师说我要回去读,他同意了。
实际上,《云中记》的稿子我读了好几天。回去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云中记》我要慢慢读。后面每一天,读到我感动的地方,我就跟他说;读到我疑惑的地方,我也跟他说,他就给我解释。好的文学作品,都有它们自己的节奏。《云中记》不是一部能快读的作品。阿来老师曾经说过,他的语感的保持,来自对古典诗歌和散文的反复阅读,从《诗经》,到《楚辞》,到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再到唐宋散文。他的作品总是有一种笼罩在文本之上的意境,大概就来源于此吧。就是这种意境让人沉浸、体味,不愿快读。
伍旭升: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祭师,书中也涉及人神交融的“天问”,有不少应当是普通人所不了解的吧?作为编辑,你有没有就此请教过作者?阿来老师又是怎样解答的?
王淑红:对,主人公阿巴是一个祭师。祭师是书面语,阿来老师说,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巫师。
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我在编《云中记》的时候,已经人届中年,在面对一种新的文化的时候,会去尝试从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的角度去理解其合理性和优越性。阿来老师写的这个地方、这个族群,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祖先,信仰山神,信仰老柏树可以通灵。我对此没有疑问,是以一种接纳的心态看待的,没有就此跟阿来老师交流过。
伍旭升:作为编辑,怎么能够树立起与名家交流时的自信心,并表现出令对方尊重和接受的专业能力?
王淑红:这个可能是编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要努力训练和提高的。也没有捷径可以走,就是平时多读好书吧,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力和判断力。
我一直觉得,真正的好作品都是作家发自内心想创作的。每一部有灵魂的作品都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都是作者内心的一种折射。作为编辑,或者作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共鸣,有感动。我会把这些让我共鸣、让我感动的部分跟作者交流、印证,真诚地交流。
这一刻仿佛群山共舞
伍旭升:这部作品有着阿来一如既往的空灵,有着触及灵魂的冲击力。我们经常说,一个作家不能感动自己,怎么去感动他人?套用一下,是否可以说,一个编辑如果自己不能被感动,又怎么感动读者?又怎么更好地传达文本的魅力?编辑过程中,你是什么感受?有哪些让你特别感动的地方?
王淑红:当然,感动的地方非常多。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阿巴祭山的时候。阿巴买了进献山神的纸马,用小云杉削好了进献山神的剑。他仿佛看到云中村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跟在身后。他唱起古老的歌谣:“什么样的水珠带着草木的香?”身后的女人们曼声应答:“露水带着草木的香!”他唱:“什么样的水珠闪着彩虹的光?”男人们齐声应答:“太阳照着露水闪着彩虹的光!”呼!火燃烧起来,烟柱直上云天,阿巴击鼓摇铃,围着火堆跳出祭师的舞步。他唱:“呜嗬嗬——东行千里绵延百代的云中村民在不在!”“我们在!我们在!”……这一刻我仿佛觉得群山共舞,山间回旋着云中村人高亢悠扬的歌声。
还有一处,阿巴在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打算种一点蔬菜,但他只是松了土,还没有撒种子:“两场夜雨过后,松开的土里就有新芽出现了,像土上起了稀薄的绿色青烟。阿巴坐在院子里久久凝视。第二天,绿色又深厚了一些。第三天,这些新绿被阳光透耀时,显得更加清新可人。第七天,阿巴发现,这些长出来的正是蔬菜,是亿万遗漏在院子里的种子,在松土后,在夜雨后,萌发了。”
这些蔬菜长起来后,阿巴睡觉就不关门了。日子过得慢,阿巴醒得越来越晚。睁眼时,刚好看见早晨斜射的阳光把那些翠绿的叶片照耀得晶莹剔透,叶片边缘上坠着的露珠闪闪发光。
……
这天,一只鹿向着他院子里的菜园走来的时候,他还没有醒来。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鹿走到只剩下半个门框的院子门口时,像人敲门一样,用前蹄叩击门前的石阶。嗒!嗒嗒!阿巴醒来。他睁开眼睛,先看见门框中阳光的帘幕。他再一次睁开眼睛,才看见那一院青翠,同时看见了鹿的影子遮住了一些阳光。再睁一次眼,把眼光抬高一点,他看到了那头鹿。它站在院门前,用前蹄轻叩着石阶。
那是一头雄鹿,今年新生的一对鹿角刚开始分叉。阳光从鹿的背后照过来,还没有骨质化的鹿角被照得晶莹剔透。鹿角里充溢的新血使得那对角像是海中的红珊瑚。阳光正像海水一样汹涌而来。
看,这是阿巴的桃花源。
是的,一个编辑首先要喜欢自己编辑的作品,才可能饱含真诚地向别人推荐。事实上,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喜欢的、欣赏的、感动的,才会发自真心地推荐给别人。
伍旭升:唯美的画卷!还有,一翻开目录页,就被目录中的时间性标题吸引住了。你审读编辑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请解读一下是否隐含着寓意和玄机。
王淑红:目录的时间性是非常清楚的,有一种乐章式的节奏,有一种首尾呼应的圆转美。目录中已经体现了,阿巴上山后,第一天到第七天,是他生命进行曲的高潮阶段,激烈高昂;而后面的第一月到第六月进入一种开阔有力的舒缓;直到最后的那一天,既是对第一天的回应,又是全曲的最高峰。回环盘旋,绕梁三月。
伍旭升:作品描写的是“汶川大地震”前后的重大灾难事件,因为编辑这本书,你又专门对汶川大地震做过了解,甚至去过震后的汶川没有?
王淑红:没有,一切通过作品看见,相信,沉浸,告慰,敬畏。
从“云中村”到“云中记”
伍旭升: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非常灵性、干净、流畅、完美,好读易读,代入感也很强,似乎让编辑费心加工的地方不是很多。请介绍一下都做了哪些具体的编辑工作。
王淑红:对,《云中记》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作品。文本部分编辑所能参与的并不多,除了基本的字词的校正,偶尔会有情节上的疏漏。《云中记》从祭师阿巴的视角出发,写他回到废墟中,回到无人的荒山,等待亲人鬼魂的出现,等待山神的旨意。阿巴在空荡荡的村子里住了半年,他的摇铃在每一个残破的院落里响起,记忆也随之不断回闪,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关于那场地震,关于他丧生于地震之中的妹妹、乡邻,甚至是更久远的关于他自己和他同是祭师的父亲,这一群人和他们生前身后的故事。这样的回忆循环往复,有时候就会出现偏差,两次提到的同一个时间段的情节可能会出现不同。比如关于地震发生时阿巴在做什么,第一次提到的时候,他正跟两匹马在一起,在山上;第二次提到的时候,阿巴正在院子里,准备祭祀的香料。这种情况,就要提醒作者修改。
剩下的就是编辑要做的常规工作,各出版社的流程应该都差不多。
伍旭升:书中的主人公身份是祭师,文中也提及是宗教工作者。但作者分寸把握得很到位。
王淑红:虽然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藏族的村子,村民们信仰的是苯教,但是我们国家尊重民族信仰,而且阿来老师的分寸确实把握得很好。但我们还是把这本书送去做了重大选题审读。这是因为,《云中记》是阿来老师继《尘埃落定》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巅峰之作,我们非常看重,对它的未来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在它出版发行的路上不会碰到任何障碍。实际上,审读的专家也认为作品没有任何问题,对作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伍旭升: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书名与章节标题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编辑能发挥作用和体现水平的地方又在哪里?
王淑红:书名、章节标题对一本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因为这两部分决定读者对文本产生的第一印象,是读者决定要不要读下去的第一判断依据。章节标题,编辑参与得少一些,基本是作者完成的。其实,长篇小说一旦完稿,再调整的话就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我们社的出版过程中,跟作者一起商量书名的调整是经常的事。《云中记》在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书名是“云中村”,因为当时阿来老师还仅有构思,小说中那个村子的名字叫云中村,所以合同上暂定名为“云中村”。后来稿子拿来后,不仅是我们出版社,《十月》杂志社也参与了书名的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换掉“村”这个字。因为“村”在近些年里,好像被附加了另一种多元的意义。我记得曾经讨论过叫“云中祭”,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书名,但我们又担心大家会有对于死亡的禁忌,因此舍弃了。最后阿来老师选择了“云中记”这个名字,既写实又有空灵的美感。
生命之美绽放神性之光
伍旭升:阿来老师本人对本书的营销有什么期待?又做了哪些配合工作?
王淑红:关于营销,阿来老师并没有提什么要求,我想这也是基于对出版社的信任吧。但是他对我们营销的配合度是非常高的。阿来老师是文化界的名家,受邀参加的活动是很多的。我记得《云中记》出版前一个月,我就跟他说,《云中记》出版后两个月的周末都为我们空出来吧,他很痛快地说好。
在《云中记》出版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做新书分享。我们先是联合《十月》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后来又陆续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做了新书分享和读者见面会。不出意外,评论界的老师们都对《云中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各大媒体也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后面就是上各种文学榜单,很多文学榜单上《云中记》都是榜首,包括月榜和后来的年榜。
2019年8月,《云中记》获第十五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4月,《云中记》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2020年5月,《云中记》获第九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2021年7月,《云中记》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伍旭升:在宣传营销时,你们重点提炼的作品的主旨和内蕴是什么?
王淑红:首先,就像写在目录前面的文字,这本书是阿来老师献给地震中的死难者和消失的城镇与村庄的安魂曲。
其次,就像阿来老师自己说的,“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陨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云中记》是一个普通人的英雄之旅,是生命之美绽放出的神性之光。后来,我们在做新书分享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命之美绽放神性之光”。
编一本好书,本已自足
伍旭升:编辑这部作品,对自己的灵魂和价值观有什么触动?本书获奖,对你的职业成长有什么意义?
王淑红:阿来老师说:“我亲历了汶川地震,目睹过非常震撼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这次地震,很多乡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是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强烈,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
《云中记》中万物有灵,作者阿来具有一种宽广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而且认为众生平等。这种生命观会令我们谦逊、慈悲,内心平和;同时,令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从容行进。
《云中记》出版后收获了非常多的重要奖项,作为本书的编辑,与有荣焉。遇到一部好作品,编一本好书,本身就会带来足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获奖是肯定,是锦上添花,对提升职业自信心很有帮助。
伍旭升:是的。遇上好作品是一种幸运,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洗礼。谢谢你的分享。
(采访者:伍旭升,中国出版集团原编委办主任,曾任《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长、总编辑;受访者:王淑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云中记》责任编辑)
来源:中华读书报 | 伍旭升 王淑红
